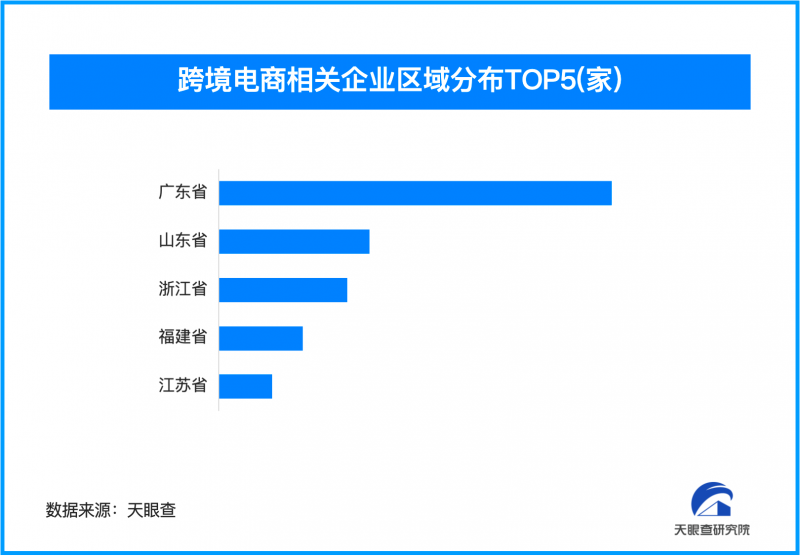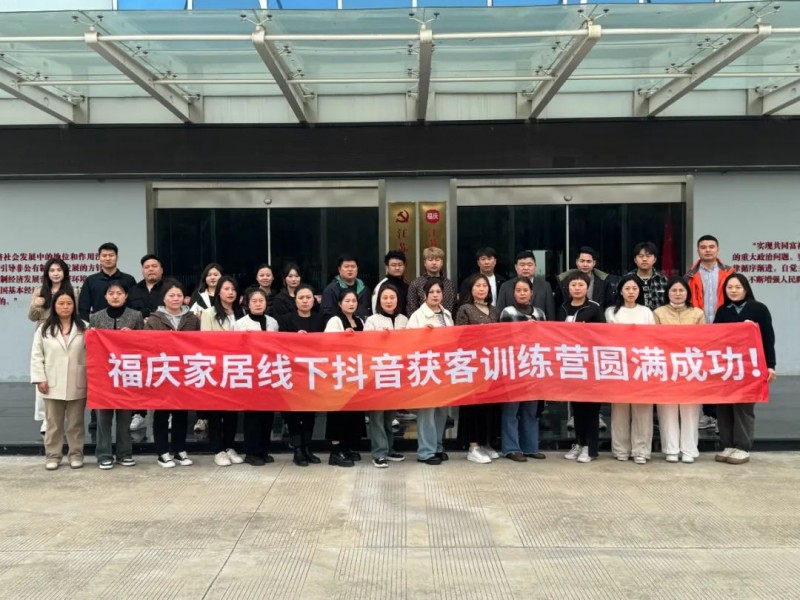元绍伟:再议天津得名
2024年5月14日 《今晚报》“津风物语”发布
永乐皇帝因“天子渡津”之故为天津赐名,此种说法经多年流传,已经近乎共识,然而此说颇有可商榷之处。
一则,从未有皇帝以“天”命名自身行迹之情况。“天”字在旧时从未作皇帝解,皇帝与“天”的关系应是“天子”。汉代以上,皇、帝、天、天子自有其关系系统,此不赘述。汉代以后,天子逐渐解作上天之子,《白虎通·爵》:“天子者,爵称也。爵所以称天子者何?王者父天母地,为天之子也。”故天子和天绝不等同。若说天是天子缩称,如“天颜”解释作“天子颜面”,则应该是自下而上角度,而不应该是皇帝自身角度。皇帝的作为或用物,应称御,如乾隆笔墨落款常为御笔等。
二则,赐名说不符合卫所命名规律。设立卫所,起始于洪武元年之前,并于洪武十三年左右定型。洪武十三年之前卫所命名,大致分为两类:一是军名,多是军中旧部名称的延续,如水军左卫、骁骑右卫、龙虎卫等;一是地点,如苏州、镇海、扬州、凤阳左、皇陵等卫。需要指出的是,地点并不等同于地名,如皇陵卫,即朱元璋父母埋葬处,而非地名。洪武十三年之后,新设的卫所几乎全部以地点命名。永乐元年二月,朝廷进行卫所调整,涉及燕山左、燕山右、天津右等六十一个卫及常山等千户所,这些卫所中,除去京师附近的义勇、神武、武成、忠义等老牌卫所仍是沿用旧军名外,其余全部为地点名,天津概莫能外。
三则,赐名是大事,理应见诸记载。若言朱棣在此渡河时当即赐名,则当时朱棣尚未登基,于情理不合;若言朱棣是登基后再赐名,因为隐讳的缘故,未加记载,那么为了隐讳就更不应该行事后赐名之举。古代皇帝赐名是大事,《起居注》《实录》等记载详细。有明一代,皇帝赐名的对象较多,既包含“远人来归,宜有以旌”的外藩或外邦族,也有功臣及子孙,甚至包含如《大明集礼》等书、龙兴寺等寺庙、“飞越峰”等马匹牲畜。各代《实录》记载了明代皇帝赐名事250例,赐姓(含名)等事50例。《太宗文皇帝实录》对天津卫设立有明确记录:“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,宜设军卫,且海口田土膏腴,命调缘海诸卫军士屯守”,但并无赐名记载。
四则,不符合明代行政制度。百姓编排故事,常将皇帝和朝廷混为一谈,但实际行政事务,必然遵从朝廷行政流程。明代朱元璋废宰相后,内阁行政制度逐渐成型。当时行政流程是百官条陈,内阁票拟呈皇帝批红,然后交地方实施,或者是皇帝授意,内阁票拟呈皇帝批红,然后交地方实施。也就是说,卫所改革及命名不应是自上而下,而应该是自下而上。永乐元年二月,令天津右卫等隶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,是天津卫所首次被记载,此次改隶,共涉六十一卫,其行政流程,同样是自下而上。况且天津有明一代只是静海县之一隅,朱棣起兵时向南千里,此处只是一小站,并无紧要干系。而天下卫所三千余,卫五百余,若言皇帝有心思关注一个卫所名称,似有不妥。
五则,“天津”为旧词,指银河畔或天津星,何又单独衍生新意?自春秋战国起,该词一直被广泛、大量使用着,如屈原《离骚》:“朝发轫于天津,”阮籍《咏怀》:“遥顾望天津,”骆宾王诗“疏派合天津,”李白诗“胡雏饮马天津水”,白居易诗“晚归骑马过天津”,司马光诗“析木带天津”,王安石诗“却含愁思度天津”等等,天津一词,古诗文中使用非常频繁。朱棣同时代文人,刘伯温诗集中30余次出现“天津”,宋濂诗“江南杜宇啼天津”,高启诗“萦贯天津若绛河”。如此广泛使用的词被赋予新意,未免儿戏。
关于天津名称的来源,笔者以为是“天津星对天津地,天津地设天津卫”或“天津星对天津地,天津地驻天津军,天津军改天津卫”。即因天津星分野在此,故此地原本即称为天津地区,《元史》载,元朝时此地河流即被命名为天津河,曾设天津巡河官,上有天津桥,周边有天津关等皆是佐证,天津地区的卫所设置,依据地点命名法,则是天津卫。或者因天津星分野,于是有天津地区,后驻扎在天津地区的军部,称天津军,然后改天津卫,如是而已。